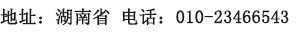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同人多将“文学变革”和“文字变革”并举,视白话文学为“活文学”,视文言文学为“死文学”。
不过,当时也有很多专家教授反对白话文。比如著名翻译家林纾,就是用文言文翻译了《茶花女》的那位,他就曾提出“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梅光迪、吴宓、胡先等著名学者,也纷纷指责胡适、钱玄同等人是粗浅的破坏分子。
从英国留学归来,曾任北大教授、北京农大校长的章士钊,就是后来因女师大事件跟鲁迅打官司的那位,他也是白话文的反对者。章教授曾以“二桃杀三士”这个典故为例,论证文言文优于白话文,不过却闹出了一番笑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且待小新为大家细细讲来。
年8月,刚刚从北京去到上海的章士钊在《新闻报》上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一文,主要目的是拥护文言文、贬低白话文。章士钊在文中这样写道:
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章士钊的意思是说,文言文微言大义节奏又美比白话文要好,就好像“二桃杀三士”这个文言典故可以直接放在诗里,毫无违和感,但如果换成白话文就没一点味道了。
不过,章士钊虽然用户文言文,但似乎对古代文化及文言文的理解并不到位。章士钊的文章发表出来之后,对古典文化深有研究的鲁迅便发现了这一点。于是鲁迅发表了《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一文》,引《晏子春秋》为证对章士钊进行了辛辣讽刺。鲁迅是这样说的:
《晏子春秋》现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这古典就在该书石印本的卷二之内。大意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个人)事景公,以勇力博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于是晏老先生以为无礼,和景公说,要除去他们了。那方法是请景公使人送他们两个桃子,说道:你们三位就照着功劳吃桃罢……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独生,也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
章士钊的脸这下可丢大了,一个口口声声拥护文言文的大教授,却连基本的古典文献《晏子春秋》都没读通,还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把文言文翻译错,简直是“叶公好龙”啊。但章士钊并不醒悟,几年后又主动翻出这回事儿,声称这本不过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是鲁迅小题大做了。
这回就连以脾气好著称的胡适都看不下去了,胡适发表了一篇杀气勃勃的《老章又反叛了!》,对章士钊进行了一番讽刺。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还宣告道:
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需求。有它本身的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
好一句“使天下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其实就是文字革命的初衷。鲁迅和胡适在思想上虽然有多对立之处,但在对白话文的态度上可以说是完全一致。鲁迅之所以一直呼吁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甚至在临终前说出“汉字不死,中国必亡”,为的就是能让更多人有机会学习文化知识,不让知识成为某些人的“专利”。
就连章士钊这样的著名学者都没能正确理解一个并不生僻的文言典故,其他人就更不要说了。更何况,当时的识字率还不足百分之二十。鲁迅对文言文对汉字的态度确实有些偏激,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为的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