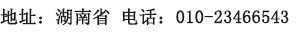刘翠玲,网名踏雪寻梦,陕西安康人,小学教师。作品散见于《中国诗歌网》《中国作家网》《安康日报》《汉江文艺》《香溪》《咸阳文艺》《陕西诗歌》等报刊网络。
用爱守望一方净土
——读朿宝荣散文诗集《穿过季节那条河》有感
那天,我拿到由朿宝荣老师亲笔签名的散文诗集《穿过季节那条河》时,心情很激动,我如获珍宝。对于一个刚刚走近文学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学习的好机会。早在几年前就读过朿老师的文章,他的文字秀美清新,超凡脱俗。读完这本诗集,让我对朿老师的散文诗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本作品主要描写作者对亲人、对故乡的眷恋和赞美,很是耐人寻味。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挚情感,优美的诗意语言,还有发人深思的人生哲理,都是这本诗集的靓点,也是我学习的地方。
一个爱好文学的人,尤其是爱散文诗的人,一写就是几十年,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到两鬓斑白的老人,这是何等的执着!朿老师经历过人生得意之时,也同样经历过人生的低谷时期。曾经为了生活,一度辍笔。然而,一旦爱上了文学这方净土,就很难再离开,内心总有一处暖是留给她的。在迷茫时,在颓废时,文学就像一块绿洲,它就在荒漠的中央静静地等你,给你希望,给你力量。散文诗对于朿老师就是这样。我被朿老师对文学的爱和对散文诗的情有独钟而感动。
散文诗是情与理的有机结合。情是散文诗的血肉,理是散文诗的骨骼。在本诗集中,朿老师用情理交融的手法写出了对故乡、对汉水浓浓的爱,这种爱是种深沉的爱。
作者心中的故乡有栀子、萤火虫、蚂蚱、蛐蛐和蛙声,有哗哗流淌的小河,有圆润的石墩,有温暖的老房子,有吱呀吱呀转的风车,有与村庄河流生死相依的那棵树……而“远去的村庄、摇曳的花朵,在记忆里渐行渐远,缩小了我赖以生存的空间”。作者离开故乡多年,房前屋后,荒草萋萋,稀薄的鸟鸣、狗吠,几近干涸的小河,颓废的老房子,废弃的旧风车,作者只有“以手为犁,迎风而歌,将痛苦的泪水和汗水滴入这片湿漉漉的土壤,那上面生长着绿叶对根的希望,直顶苍天。”“与一棵树长久的对话,需要彻夜长谈。在生存的方式里,讲述那些背太阳的人,如何面朝黄土,背朝天,隆起山一样的脊梁,把黑夜背到黎明,把夯音甩来甩去,把痛苦挨在心底,直到春播秋收。”
在汉江面前,“我是一块不起眼的鹅卵石,在水的滋润下,光泽日渐红润,组成了人生一面风景。”“在日月的打磨中,我从生活的底层复出,白玉无瑕般呈现在万人眼前。你的点化让我深谙为人之道,你的雕饰让我身价倍长,你的发现让我重见天日,而我的爱呀,像凤凰涅磐般再次燃烧。”(《穿过季节那条河》)汉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在朿老师笔下,汉江更是生养我们的最伟大的母亲,我们要用大爱守望汉江。我们的喜怒哀乐,都可以与之倾诉。看到滔滔江水日夜奔流不息,我们有理由抛掉烦忧,迎难而上,超越自己。汉江以博大的胸怀养育我们安康儿女,我们有责任去热爱她去保护她。
散文诗的语言形态是独特的,它既不是诗歌的纯诗化语言,也不是散文的那种散漫型描述语言,而是一种准诗化或者说是泛诗化语言。诗集中,朿老师用朴实、感人的语言,使文章充满意境,充满诗意。
“如果说阳光能织出七彩的线,我想那和妈妈纺出的没有两样,缝在我胸前的纽襻,扣在我身上,紧在妈妈心里。”这是散文诗《妈妈》中的一段。在朿老师心中,妈妈就如阳光,能织出七彩的线,给“我”温暖,给我“安全”,给我一个完整的“家”。这里运用形象的比喻和诗意的语言,表达出母亲对儿子无私的爱,和儿子对母亲深深的感激。
“回家的日子,是用手指一节一节掐断。其实,日子是一根透明的丝线,系着远方的山峦。”这是《栀子花开》中开头的一段,用“掐断”一词,生动形象地写出游子一次一次决定回家,又一次一次打消这个念头的无奈。“回家”成了他们朝思暮想心心念念的事。但为了生活,只得选择漂流他乡。把“日子”比喻成“透明的丝线”,既形象地说出了“日子”悄无声息地流过,又点明游子心系故乡渴望回家的思乡之情。
“你把眼泪织成希望,织成白云,挂在耸入蓝天如臂的桅杆,用目光抚平浪礁,剪掉雷电,遮住风雨,采摘一片阳光涂抹在我的身上,搓一把长长的思念化作一根二月放飞风筝的线,变作古道纤夫们脊梁上拉直的纤,和我在风雨中在长夜中同行……”《白帆船》中的一连串动词,“织”“挂”“剪掉”“遮住”“采摘”“搓”等,极富画面感,绘出了“你”跟随“我”如影随行,相濡以沫,与“我”同风雨共命运的感人画面。
散文诗是情感、哲理与诗意的语言三者的统一。朿老师就是善于从社会底层、生活细微处挖掘诗意,作品富含哲理,充分反映了朿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