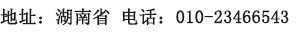1
刚下过雨,小巷里的青石板湿嗒嗒的。
“这就是莲花巷了,路有点滑,且慢些行。”专司庄产买卖的牙人热情引着主顾往巷子深处走。
“多谢。”
来客是外地口音,衣着整洁却不华贵,身边只一个长随,一看就是刚调来京城任职的小官。
于是牙人笑道:“老爷初来乍到,想是不知京城东贵、西富、南贫贱……”
陪同看房者的长随忍不住插嘴:“那北面呢?”
不等牙人开口,看房的老爷便道:“蠢物,北面是皇城。”
那长随打了个颤,低头噤了声。
牙人侃侃而谈:“莲花巷地段好,往东,去六部衙门不远,往西,去各坊市也近。”
还有一句话牙人没有挑明,莲花巷除了位置当道,里头的宅子布局紧凑占地不大,最适合囊中羞涩却装点门面的各部堂小官。
“这么好的地方房子不好出吗?”长随嘀咕了一句。
“莲花巷的房子当然好出,今儿带你们看的这座宅子,屋主家里出了事,急着用钱,正好叫你家老爷遇上了。”
“可否详谈?”
买房图个吉利,可不能贪便宜买了凶宅回去。
牙人把声音压低了些:“这家老爷叫徐启平,是国子监的司业,正六品,半月前因着贪墨银两叫京兆府给拿了。听说,昨儿个被大理寺提走了,一家子女眷束手无策,只能卖房筹点钱款,想着拿钱把亏空补上,好争取个轻判。”
“大理寺提了人?那这事可不小吧。”
大理寺司邢狱重案,这案子从京兆府移交到大理寺,看来不是贪墨银两那么简单。
“老爷是懂行的,所以这徐家是真急呀,想趁着案子没判下来,寻个好卖家,只要给得起现银,价钱好说。前头就到……”房屋牙人说着,伸手朝前指着,忽然愣住了。
徐家宅门紧闭,似闭门谢客,门口却停着一辆高大的黑色马车,套着两匹威风凛凛的骏马。
这般规制的马车可不是住在这里的人家用得起的。
牙人微叹,今日这买卖怕是做不成了。
……
徐家宅子里,老太太坐在正堂中,望着眼前的来人,疑惑道:“你,真有办法把启平救出来?”
徐启平是国子监的司业,官职不高,俸禄不多,傍着徐家祖上的薄产,在莲花巷中日子过得算是不错的。
半月前,徐启平遭人告发,说他贪墨银两,人证物证俱全,当即被京兆府收监。徐家老小战战兢兢地在家里等消息,昨日有亲故递来消息,说徐启平被大理寺的衙差提走,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徐启平区区一介六品官,素日往来不是高官大员,一遇着这事,旁人便是有心相助,也无能为力。
正在徐家一筹莫展之计,有人上门了。
来人一袭华衣,长得斯文儒雅,一开口却是尖声尖气的调调:“老太太放心,徐大人的案子我家主子已经看过了,涉案的银两不多,区区几百两银子,只要你把二姑娘交给我,今晚子时我就能把徐大人毫发无损的送回来。当然,贪墨之事一笔勾销,徐大人还能官复原职。”
说着,那人笑道:“今儿徐太太跟着我进大理寺探望了徐大人,老太太不会对我家主子的手段心存怀疑吧?”
老太太抬手揉了揉眉心,苍老的脸庞却绷得更紧。
徐启平被收监后,徐家人使了各种法子通融打点,想去探监,可每回都无功而返,今日来人领着徐家主母去往大理寺探监,顺顺当当了见到了徐启平不说,大理寺的狱卒待徐家的人竟是恭敬有礼,对方的权势足以滔天。
徐老太太看到了一丝希望,却又感到十分的绝望。
那人最善察言观色,自是看出老太太已经意乱,侃侃道:“徐大人是老太太的独子,我家主子要的,只是徐家的一个庶女。没有了孙女,老太太固然伤心,可若没有徐大人,往后这一大家子还能活吗?我听说,今日老太太已经请人帮忙卖宅子,卖了房子的确可以补上贪墨的亏空,可贪墨不是借支,大理寺也不是使银子就能打点的地方。”
对方句句在理,步步相逼,听到这个,徐启平的嫡妻陈氏忍不住道:“母亲,唇亡齿寒,若是老爷定了罪,我们这家子往后都没活路了。”
徐启平这一辈,只得他一个男丁,好在他有妻有妾,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算得上是人丁兴旺。老太太的两个孙子尚在读书,若是徐启平真问了罪,孙辈的科考之路就断送了,余下的女眷能坐吃山空多久?
沦为犯官家眷,所有人的前程都没了,男丁不能科举,女眷不得婚配。
见老太太始终不肯言语,陈氏扑到老太太跟前,哭求道:“母亲,儿媳知道夫君是受奸人所害,可他已然落入别人套中,根本无法辩白,牺牲一个庶女,救徐家于水火,您为何还不答应?”
“闭嘴!”老太太重重拍了一下桌子,悲愤斥骂,“我们徐家是诗书人家,绝不会卖女儿求生!”
“难道母亲要眼睁睁看着徐家毁了么?”陈氏见老太太不愿松口,大哭起来,索性当着外人将心中的话一股脑说了出来,“您老就是偏心,儿媳知道您一直心疼幼宁,平日里只疼她也不疼姝儿也就罢了,难道在您老人家眼中,徐家上上下下十几口人加起来都比不上幼宁一个么?”
“闭嘴!”老太太狠狠打了陈氏一嘴巴。
陈氏嫁进徐家二十年,还是头一遭挨了婆母的责打,捂着嘴巴愣住了。
来客听着婆媳俩的对话,神情淡漠,待屋子里的动静稍停,方道:“老太太,成与不成,您老给个准话。”
陈氏回过神,跪在地上,砰砰朝徐老太太磕头。
老太太眸中含着眼泪,摇了摇头:“我做不了这个主,幼宁的事,听听幼宁是怎么说吧。”
陈氏听她语气松动,起身拿帕子拭去眼泪,转身对身边的妈妈道:“老太太的话你听到了,请二姑娘过来说话。”
二姑娘徐幼宁,是徐启平外室所生,抱回徐家的时候尚不足两岁,说是生母身子孱弱,产后一年多便没了。那时候陈氏正在坐月子,不肯照料这来路不明的外室女。老太太见孩子可怜,便抱到了自己院里,取名幼宁,养了几个月,越发觉得亲昵可爱,遂把她一直留在身边。
老太太住正屋,幼宁住在旁边的暖阁里。
顷刻,这位二姑娘便被领了过来。
她一到,初时神情傲然的来客顿时眼前一亮。
徐幼宁年方十八,正是待字闺中的年纪,她身上穿着杏色袄裙,外头罩着一件水红色比甲,发髻梳得整整齐齐地,清秀文静的模样,看起来像枝头开得最端正的一朵杏花。
屋子里站着生人,徐幼宁不安地看向老太太:“祖母……”
老太太见着她,原本一直克制的眼泪顿时流了出来。
徐幼宁吓了一跳,忙拿出帕子给老太太擦眼泪,惶恐道:“祖母,您别担心了,便是不能住在这宅子里头,咱们一家人搬去乡下也是极好的。”
徐启平入狱,徐家上下日夜不安。
卖宅子的事,徐幼宁虽然没有插手,也是知道的。方才婆子来叫她的时候,她正在暖阁里收拾自己的东西。
如今见屋子里有生人,她心下以为这是祖母托牙人寻的买主了。
陈氏见状,拉过徐幼宁的手,将波动的情绪强行平复下来,和蔼道:“幼宁,现在有一个救你爹爹的法子,你愿意救他么?”
“我?”徐幼宁听得疑惑,手指不安地绞在一处,“太太,我怎么救?”
徐启平有外室这事,陈氏一直耿耿于怀,不愿意让徐幼宁叫自己母亲,她便一直尊称陈氏为“太太”。
陈氏牵着她走到那来客跟前,“这位先生有法子救你爹爹。”
徐幼宁转头看向那陌生的客人。
来人一袭玄色衣裳,上头没有任何花纹,她说不出他身上挂的玉佩是什么明堂,可她瞧得出他衣饰打扮比他们一家子金贵得多,举手投足比爹爹在国子监的同僚们还气派得多。
她有些茫然,只是陈氏怎么说,她就得怎么做。
于是朝着客人拜了一拜:“先生,请您救救我爹。”
来人本来神色漠然,始终带着高高在上的傲慢,听到徐幼宁这略带稚气的话,端着的气势不禁减去几分,柔声对徐幼宁道:“二姑娘,正所谓礼尚往来,我若帮了你家的忙,你是不是也该帮我的忙?”
是这个理。
徐幼宁点头。
“这么说,二姑娘答应了?”客人问道。
不等徐幼宁说话,老太太便道:“幼宁,他不是要你帮忙,是要带你走!”
带她走?
徐幼宁愈加迷糊,望着客人问道:“先生要我去你家做奴婢吗?”
“是伺候人,但不用做奴婢。”
不用做奴婢,却要伺候人……徐幼宁养在闺中,却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她望着客人:“先生是要我去做给你做姨娘吗?”
2
来客听得笑了。
“不是伺候我,也不是做姨娘。”
徐幼宁糊涂了,“那我做什么呀?”
她是外室之女,陈氏嫡出的三姑娘跟她吵架的时候就说过,她这样的庶女只配给人做姨娘。
来人原想着尽快将人忽悠走了交差,见到徐幼宁这副娇憨可怜的模样,不忍欺骗,“主家要你过去伺候,只是伺候,没有什么名分的。”
哐当——
徐老太太手一抖,手中的茶杯摔落在地上,她忽然双拳紧握,用沙哑的嗓子怒吼道:“出去!给我出去!”
她可以让自己狠下心顾全大局,也可以告诉自己舍弃了孙女是为了保全家族。
可是当她亲耳听到别人对疼爱的孙女说那样的话,她再也无法忍耐下去。
客人并不生气,依旧维持着风度,悠然道:“老太太不必动怒,伺候我的主家,并不辱没二姑娘。今日接去只是伺候,若得主家喜欢,将来会有天大的前程。”
说罢,他转向徐幼宁,目光中尽是怜悯。
“老太太觉得我的话刺耳难听,将来徐家败落,更难听更刺耳的话还在后头呢!”
老太太正想反驳,那人继续道:“倘若大理寺重判徐大人,徐家的女眷充作官婢不是没有可能。”
若说之前他是劝说,最后这一句却是直截了当的威胁。
对方的主子有本事影响大理寺的判决,徐启平的命运已经被对方死死捏住了。
老太太的嘴巴动了动,终究是颓然地往后一坠,面如死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来人见目的达到,欣然一笑,转向徐幼宁:“二姑娘,你觉得呢?”
徐幼宁不指望什么前程。
她念书不多,诗词都不太精通,女红不好,只能做帕子这样简单的绣件,嫡母陈氏总说她不太灵光。
但客人特意对她说的话,她听明白了。
今日她可以拒绝不跟着他走,可等爹爹被大理寺审完,徐家败落,她的下场好不到哪里去。
明白是明白,一时之间,徐幼宁对“伺候人”这桩事还是有些懵。
她下意识地回过头,茫然看向自己最熟悉和最敬爱的祖母,想寻求她的帮助,但老太太正捂着脸哭泣着,没有看她。
陈氏倒是在看着她,目光灼灼,眼神笃定,菜市上的屠户会这样看着案板上的肉。
徐幼宁不喜欢被这种眼神看着。
她收回目光,垂下了眼眸。
陈氏的目光让徐幼宁弄懂了眼前的局面,祖母和太太既然把她喊出来了,那就是已经做出了决定。
在徐家,她没有做决定的权利。
若是苦苦哀求祖母,只会叫场面难堪。
“二姑娘,你觉得如何?”
还是陌生来客打破了屋子里的僵局。
他生得白净斯文,只是脸上没有一根胡须,徐幼宁看着有点不习惯。
“先生,要是我跟你去了,我爹真能回来么?”
“那是自然,只要你跟着我上了马车,子时之前,你爹就能回家。”
徐幼宁低头思忖片刻,转过身,跪在地上朝叶老太太磕头:“祖母,往后幼宁不能在您跟前尽孝,您老人家要保重身体。”
老太太依旧掩面而泣,什么话都说不出。
徐幼宁见祖母哭得伤心,只好转身对陈氏道:“太太,祖母年迈,幼宁无法在祖母膝下尽孝,往后求太太把幼宁这一份尽上。”
陈氏脸色一直阴沉,听到徐幼宁这话顿时怒道:“你是说我不事婆母么?”
“不是的,太太,我只是想请……”
陈氏说罢,还不解气,又道:“你要救的人,是你亲爹,你不救他,徐家没了,你能独善其身么?老太太不想你去,你心里惦记这个惦记那个,索性别去了,等着你爹下狱,看看卫家还会不会来聘你!”
卫家……
祖母心疼幼宁,早早地就给幼宁定了一门好亲事,今日一走,卫家这亲事指定要退的。
“太太,我的亲事还得劳烦您帮我退了。”
陈氏的眸光一闪,脸上的怒气稍稍收敛了些:“这些话不用你说,该做的我自然都会做。”
“谢谢太太。”徐幼宁并没有因为陈氏的训斥而变色,至始至终,她的脸色都很平静,甚至还挂着一抹笑。她向陈氏行了一礼,又朝着祖母磕了一个头,这才转身:“先生,我进去拿我的东西。”
想着要搬去乡下,徐幼宁今日便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妥当了,这会儿要走,倒也方便。
“什么不用带,走吧。”
客人伸手做了个请的手势,语气却没有半分商量的余地,徐幼宁吸了口气,跟着他出了门。
两人登上了停在徐家门口的那辆大马车。
车身黑漆漆的,罩着黑色的帷布,前头套着两匹彪悍的高头大马,气势汹汹地打着响鼻。因着他们自宅子里出来,马车上跳下来两个身强力壮的车夫,在马车前摆了脚凳。
徐幼宁素日乘的,都是只套一匹马的车,车夫也不会出来摆脚凳。
只是接她罢了,都这么大的阵势,对方一定十分了得。她心下稍安,想必这一去是真能把爹爹救出来的。
马车外头黑漆漆的,看不出一点装饰,挑开车帘,里头珠帘绣幕另有天地,香帕、茶具、坐具样样齐全,比徐幼宁住的暖阁还要宽敞。
徐幼宁看着绣工精致的软垫,有一些好奇,有一些忐忑。
刚坐稳,宅子里就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
“宁宁!”
是祖母的声音,她老人家追出来了吗?徐幼宁心口有些发酸。
“二姑娘,要下去说句话么?”那来客难得地问。
“不用了,先生,走吧。”
徐幼宁的鼻尖有些红,脸上却挂着笑。
那人看着徐幼宁神情,想说点什么,终是什么都没说,只吩咐了一声,外头马夫鞭子一甩,马儿嗒嗒地跑了起来。
马车平稳地驶着。
徐幼宁端坐在马车里,安安静静的,也不东张西望,只是眼神有些。
“二姑娘,你可有什么想问的?”
疑惑,徐幼宁自然有很多。
正因疑惑太多,一时不问什么。
于是她摇头。
那人笑了笑:“你就不好奇我要带你去哪儿?”
徐幼宁垂着眼眸,像一朵被雨打垂的芭蕉叶,一双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还是不吭声。
他打趣道:“要不是头先在你家里听你说过话,我都要以为你是个小哑巴呢!”
“我怕说错话。”徐幼宁实话实说。
“无妨,我也只是个下人,咱们随便聊聊。”
只是个下人,便有如此派头。
徐幼宁听他说话,比在徐家的时候客气许多,于是道:“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去哪儿都没什么分别。”
一问一答之间,他对这个本来不太起眼的小姑娘起了兴致,看着呆呆笨笨的,话语里倒透着通透劲儿。
又问:“我看得出老太太不想送你走,你为何不求着她把你留下来。你家里人若不乐意,我绝不会强行把你带走。”
至少今日,他不会强行把徐幼宁带走。
“祖母舍不得我,可是这事关徐家上下安危,不是舍不舍得的事。”徐幼宁答得简单,话语却令人心疼。
那人原本只想逗逗她,以解途中之乏,听到此处却想说点什么话来宽慰这个小姑娘。
饶是他平素长袖善舞,望着这么个懂事又可怜的小姑娘,也不知这种境况下到底该说什么。
顿了顿,方道:“你不必害怕,先前我没有骗你,我家主子不是凡人,是天上人,京城里许许多多的贵女都想伺候我家主子,却连见一面都难。”
这人说话真有意思,他的主子真要是人人争抢的人,为何还要兜这么大圈子要自己去伺候?
徐幼宁稍稍恢复了些精神,问道:“先生,我家里的事,您怎么都知道?”
“别叫我先生了,叫我王公公。”
公公?
徐幼宁张了张嘴,可喉咙像卡了东西,一点声音都发不出。
带走她的人居然是公公?那他的主家……
那位王公公笑吟吟的,跟先前在徐家的时候截然不同:“这回有想问的了吗?”
“王公公,你要带我进宫去伺候皇上吗?”徐幼宁鼓足勇气,怯生生的问。
“你这小丫头呀,看着憨憨的,倒是招人喜欢。”那王公公越发和颜悦色,“别害怕,今儿不是带你进宫,更不是去伺候主子万岁爷。”
来徐家要人之前,王福元早已经徐幼宁的一切摸得清清楚楚。
她的喜好,她的出身,她的性格,她的亲事,乃至她那稀罕的生辰八字。
王福元继续道:“一会儿到了地方,主子说什么你就答什么,别多问,别多看,不会有事的。”
依着王福元素日的做派,决计不会多说这一句,只是因着徐幼宁看着是个懂事讨喜的姑娘,才叮嘱了一番。
“我记住了。”
徐幼宁忽然沮丧起来。
难怪先前王公公对祖母说,即便是给他的主子做通房,也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机会。
徐幼宁从没想过自己会跟宫里牵扯上关系。
上一回去庙里祈福,碰到国子监祭酒魏大人家的姑娘,看徐幼宁姐妹就如看下人一般。魏大人是从四品的官员,已是令爹爹都仰望的大官了,宫里……徐幼宁不敢想象。
那些大人物一句话,是不是就能要了徐家所有人的命?
她低下头,不再说话。
她是来救爹爹的,若是说错话,把自己搭进去,爹爹也救不出来。
王福元见她这般模样,明白自己的叮嘱吓着她了,只是徐幼宁命运未定,害怕些总比无知无畏要强。
此后一路无话,等到马车停下,已是一个时辰之后了。
“二姑娘,咱们到地方了。”
王福元先走下马车,回头扶着徐幼宁下车。
茫茫夜幕降临,路上看不到行人。
入眼是一座高大的宅门,黑漆漆地望之令人生畏。
应当不是皇宫,戏文里说,皇宫是金碧辉煌的。
这宅门虽然高大,并不是金碧辉煌的。
“二姑娘,往这边来。”王福元见徐幼宁定定看着正门,朝徐幼宁招了招手。
徐幼宁赶紧收回目光,低下头,跟着王福元从旁边的侧门走。
侧门里头有人候着。离近了,方看清是两个表情凝重的嬷嬷,一个方脸,一个圆脸,长相不同,俱是举止沉稳端庄。
见徐幼宁进来,二人飞快地扫了一眼,低声对王福元道:“主子娘娘到了。”
3
“主子怎么来了?”王福元颇为吃惊。
出宫之前,主子说好此事交给他全权处理,怎么还是过来了?
嬷嬷无奈道:“娘娘不放心。”
兹事体大,慧贵妃哪里能在宫中坐着静候佳音。
徐幼宁低着头,听着他们说什么“娘娘”、“主子”的,越发不安,交叠在一起的手掌捏得越发攥得紧。
难不成他们要自己去伺候的是一个什么娘娘?若真如此,倒也不错,她素日就在祖母身边伺候着,端茶倒水她都会。
王福元看了徐幼宁一眼,见徐幼宁一脸迷茫,却依旧乖巧站着,更喜欢了她几分。
主子虽是暴脾气,见到徐幼宁这样水灵的小姑娘,应当怜惜疼爱的。
“二姑娘,走,咱们去拜见慧贵妃娘娘。”
一行人乘着夜色继续往前走。
方脸嬷嬷提了羊角灯走在前头引路,徐幼宁和王福元走在中间,圆脸嬷嬷走在最后。
徐幼宁在心里念叨了两遍“贵妃娘娘”。
一个时辰之前,她在自家暖阁里收拾东西,等待着明日跟随祖母搬去乡下老宅。但是现在,她居然要去拜见贵妃娘娘了。
她深吸了两口气,依然觉得心跳得很快。
王福元待她和和气气,先前跟他在马车里坐着,并不多么紧张,现下一前一后多了两个板着脸的嬷嬷,等一下还要去拜见贵妃,愈发不安。
如此忐忑着走过了两座院子一条游廊,终于站到了一处院子门口。
“王公公回来了。”守在门口的太监望见王福元,目光在徐幼宁身上打了个转儿,“娘娘正等着呢。”
王福元颔首,领着徐幼宁朝里头走去。
夜风裹着花香扑面而来,徐幼宁吸了一口,忍不住朝旁边望去。
院墙边的一排异花,正在月光下争奇斗艳吐露芬芳。
她牢记王福元在马车上的叮嘱,只看了一眼便迅速收回目光。
如此走到廊下,另有人在那里守着,这回不是太监也不是嬷嬷,而是两个妙龄宫女。她们俩什么都没说,也没有看徐幼宁,神色淡淡地打开了门。
进门是一座金桂树座屏,徐幼宁不敢抬头,跟着王福元绕过座屏往屋里去,始终垂眸看着地下,只看得见自己的脚尖和王福元的脚后跟。
屋子里的味道比花园里更好闻,徐幼宁忍不住吸了两口,又赶紧屏息,生怕自己呼气的声音太重惹怒了那位神秘的慧贵妃。
地面铺的是深灰色地砖,徐幼宁不知道这是什么材质的石头。这地砖擦得铮亮,甚至能照见她局促的脸庞。
“娘娘,人带过来了。”王福元恭敬道。
徐幼宁心里怦怦直跳,愈发地紧张,只听得一声漫不经心的“喔”。
“徐二姑娘,抬起头叫贵妃娘娘瞧瞧。”
是王福元在对她说话,徐幼宁不知这位慧贵妃娘娘会叫自己去伺候何人,只是事已至此,她只能横下心,抬起了头。
这一望,便呆住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国色天香的大美人。
她懒洋洋的横卧在美人榻上,绣着金线的裙摆垂到了地上,皓白修长的手指摸着另一只手的蔻丹,轻飘飘地朝徐幼宁这边扔了一个眼神。
屋子里橘红的烛光恰到好处地给她渡上了一层莹润的光泽,一抬手,一扬眉,皆是风华万千。
即便徐幼宁身为女子,对着这大美人亦忍不住心惊肉跳。
便是那睥睨而来的傲慢目光,也没有令徐幼宁丝毫的不适。
因她这般的仙女,原就是该这样看着凡人的。
王福元轻嗽一声,徐幼宁回过神,依着王福元先前的叮嘱朝着贵妃福了一福。
“民女给贵妃娘娘请安。”
慧贵妃眼眸微眯:“看着倒是干干净净的。”
干净?
徐幼宁听过街坊四邻对自己的评价,夸赞的一般说她秀气白净,贬损的一般说她透着小家子气,却没人用干净来说她。
这个说法,像是她是被王福元从外头捡回来的家伙事一般,人家见了这来路不明的东西,先看是不是干净的。
王福元恭敬道:“徐二姑娘的爹爹是国子监司业,他们家是书香门第,门清风正的。”
慧贵妃微微颔首,不无感慨道:“出身低了些,不过既是读书人家,勉强称得上清贵。”
徐幼宁明白,自己是王福元从外头买回来的一件货物,现在这件货物献给了主家,由着主家对货物品头论足。
从前在家里跟嫡出的妹妹妹徐幼姝争执的时候,徐幼姝总爱骂她是外室女,只配给人做妾,白占了祖母说的好亲事。
怕是连讨厌自己的徐幼姝都没想到,自己沦落到连妾都不如的地步。
只是一件货物。
“你盯着本宫做什么?”大美人秀眉一拧,忽然不悦起来。
徐幼宁心头一凛,这才收回目光,老老实实地回道:“民女没有见过像贵妃娘娘这么美的人。”
慧贵妃闻言,顿时转怒为喜,哈哈大笑起来。
因着这句话,慧贵妃似乎对徐幼宁有了兴趣,秀致的眼眸一抬:“本宫且问你,今日过来这里,是家里人逼着你来的,还是你自己乐意来的?”
徐幼宁没料到贵妃有此一问,默了一下,方答道:“是我自己乐意来的。”
慧贵妃盯了她一眼,似是看透了一切,冷笑了声:“来这里做什么的,你清楚吗?”
徐幼宁不太清楚,但她明白,若是说不清楚,只怕贵妃会更加生气,只好把王福元透给她的只言片语拼凑到一起回话:“我是过来伺候王公公的主子。”
慧贵妃听着她的话,扬起下巴,倨傲道:“懂怎么伺候男人吗?”
徐幼宁便是想编,也编不出来,只能红着脸摇头。
“罢了,带下去沐浴,剩下的交给李深。”
徐幼宁不知道李深是谁,也不敢搭话,垂眸站了片刻,很快有宫女上前,领着她下去了。
待闲杂人等退下,贵妃收起了脸庞上的懒散,眸光变得锐利起来:“人没错吧,可看准了?”
王福元道:“这徐二姑娘是外室所出,生母早亡,生辰八字只徐启平一个人知晓,大理寺那边使了许多法子盘问,徐启平都是说的这个,奴婢为求稳妥,派人送了二姑娘的画像和生辰八字去给清玄子大师过目。”
“他怎么说?”
“他说咱们找对了人。”
听着王福元的话,慧贵妃国色天香的脸庞上渐渐露出一抹恨意。
若不是清玄子这个妖道在皇帝跟前胡说八道,她哪里费得着这么大的功夫去找一个小门小户的姑娘过来给儿子侍寝?
慧贵妃从来不信鬼神,不相信他的占卜,偏偏皇帝相信,如今朝野和后宫谣言四起,她和儿子只能陪着这妖道胡闹下去。
好在王福元带回来这姑娘乖巧清白,若是真找回来什么青楼女子,慧贵妃便去把那妖道的玄天观给掀了。
“娘娘,殿下到了吗?”王福元恭敬问道。
“到了,比我还早一刻!”慧贵妃望见王福元似有忧虑,横他一眼,“你担心什么?”
王福元见慧贵妃瞧出端倪,欠然道:“奴婢怕太子殿下心里有疙瘩。”
他说得委婉,但慧贵妃明白他的意思。
她的儿子贵为太子,是何等尊贵,如今被流言所累,逼着跟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子行周公之事,心中岂会甘愿。
“本宫压根不担心这个,”慧贵妃漫不经心地撇了下唇,端起矮几上的茶啜了一口,缓缓吐着气,“为了东宫这个位置,本宫和他战战兢兢地走了十年,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见贵妃心情轻松了许多,王福元顺着她的心意说下去:“奴婢原也担心殿下委屈,后来见着这二姑娘,心里倒踏实了,模样好,性情好,是个聪慧有福气的姑娘。”
“你倒是喜欢她。”慧贵妃横了王福元一眼。
“娘娘说笑了,娘娘难道不是跟奴婢一样喜欢她吗?”
“小门小户的,小鼻子小嘴儿,哪里都不出挑,好在也没有哪里不好。左右京城里只有她的生辰八字相合,只能将就些,”贵妃淡淡道,“只不过她跟本宫一样,都是被家里人卖出来的,且叮嘱他们照顾好她,别叫她吃苦头。”
“奴婢晓得了。”
主仆二人说了会儿话,宫女领着沐浴过后的徐幼宁回到了贵妃跟前。
徐幼宁活了十八年,还是头一回在温泉池里沐浴,热浴过后,脸蛋红扑扑的,比头先见着更加水灵。
贵妃望着她,朝她勾了勾手。
徐幼宁上前跪在贵妃跟前,贵妃朝王福元使了个眼色。
王福元从旁边端出一个锦盒,打开了送到徐幼宁旁边。
徐幼宁打眼一望,盒子里头摆着一颗褐色的丹丸,闻着有一股淡淡的药香。
“你怕疼吗?”慧贵妃问。
徐幼宁老老实实点头。
王福元笑道:“二姑娘,这是娘娘赏你的好东西,既是怕疼,便吃了吧,吃了一会儿就不疼了。”
徐幼宁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一会儿为什么会疼。
今日不知道怎么回事,别人都给了她许多选择,可每回选择的时候她似乎都没得选。
她觉得,不管一会儿发生多可怕的事,能不疼也是好的。徐幼宁伸手拿起那颗丹丸,咽了下去。
不苦,只是有点梗。
慧贵妃的眸光愈发深邃,盯了一会儿,终是浅浅笑了下:“去吧,本宫希望你是个有福气的。”
王福元在心中微微一叹,朝外头一挥手,立即有宫女扶着徐幼宁起来。
徐幼宁初时不懂,为何会有两个宫女搀着她,可等到出了屋子,方才觉得头重脚轻,眼神越发飘忽,全凭着宫女扶着才不至于摔倒。
模模糊糊地,她由着宫女把自己带到了另一座小院,困意越来越浓。
在她快要失去最后一分清明时,一个高大的黑影出现在了帐子外头。
4
徐幼宁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梦里有一个陌生的男子。
男子面容模糊,手指似玉像一般冰冷,与她百般亲昵,却不曾与她说一句话。她曾以为来人是同她定亲的卫承远,然而很快就意识到,卫承远对她百依百顺,不会不理她。
他们彼此无言,却相拥着做了最不可言说的亲近之事。
不止一次。
贵妃没有骗了,她一点也不觉得疼,只是有些没完没了。
梦里风光潋滟,有淡淡的香气,有氤氲的烛光。
在迷蒙的梦境中,徐幼宁渐渐沉沦,迷失了自我。
……
睁开眼睛的时候,身边空无一人。
果然是个梦吗?
徐幼宁想要起身,发觉身上酸得要命,一点力气都没有,除此之外,身上还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所以,不是梦?
仰仗贵妃恩赐的那个丹丸,昨夜那个梦虽然谈不上是美梦,至少不是噩梦。
她记得,在梦的最后,那人抱起她,把她放进了浴桶。
在温热的浴汤包围下,她沉沉睡了过去。
也不知是什么时辰了。
她躺的这方榻十分宽敞,她往左滚了两圈,没碰到榻边,又朝右滚了好几圈,方才摸到榻边,睁着眼睛发起了呆。
昨夜那人到底是谁?
不管他是谁,能被王福元称作主子,一定是皇亲国戚。
堂堂皇亲国戚,为何非要找她伺候?
论姿色论才情,论家世论品德,在京城里她徐幼宁根本排不上号。
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有自己这样一号人物的存在呢?
昨晚那个人,今晚还会来吗?
徐幼宁的耳根骤然烫了起来,越想越觉得心乱如麻。
呆了好一会儿,方缓缓坐了起来。
这是一间十分宽敞的卧房,屋子里只这一方榻,光这榻便有徐幼宁从前住那暖阁大小。正对房门的一边摆着一架仕女围屏。
“有人吗?”徐幼宁喊了一声,无人应答。
她扶着榻站起来,除了腿很酸,背也很僵,连伸了两个懒腰才觉得好受些。
绕过围屏,看到房门紧闭。
一扭头,她发现屋子的左边是可以推开的活页门。她往走过去,拉开门,惊喜地发现外头是一个小池塘,从屋子走到池塘边铺了石板,两旁栽满了奇花异草、芬芳满园。徐幼宁勉强认出几株茶花,却不识得到底是什么品种。
她腰酸得紧,根本使不上劲,站一会儿便乏了,顺势在台阶上坐下。
正发着呆,背后有人推开门。
徐幼宁转过身,见是一个宫女打扮的女子,依稀记得这是昨夜伺候她沐浴的其中一个。
那宫女见徐幼宁坐在廊下,笑道:“姑娘坐在那里怕是有些冷硬,要不要奴婢取个垫子过来?”
说是这么说,那宫女站在那里根本没动。
徐幼宁识趣道:“不用了,这样就好。”
那宫女似乎满意徐幼宁这样的回应,又道:“奴婢桂心,奉慧贵妃娘娘之命在此伺候姑娘,往后姑娘有什么事只管吩咐奴婢。”
“多谢桂心姐姐了。”
桂心轻笑了下:“姐姐可当不起,姑娘叫桂心就成。”
“好。”
徐幼宁看得出,桂心虽然一口一个姑娘喊着,心里根本没拿自己当主子。
她倒没什么说法。
自己如今这境地,还不比人家做奴婢的强呢!人家是正经宫女,自己呢,不是宫女,不是主子,什么都不是。
经历了昨夜那般事情,徐幼宁又渴又累,于是道:“桂心,我有些饿了,能给我送些吃食吗?”
“姑娘稍等,奴婢这就去拿,”桂心道,“桌子上有茶,姑娘渴了可以先喝着。”说着便退了下去。
屋子的一角摆着一方几案,上头搁着一副茶具。
徐幼宁走过去,喝了一杯。
茶是凉的,但她顾不上这么多,她的嗓子眼都快冒烟了,咕噜咕噜喝了三杯才觉得舒服些。
她在几案边坐了一会儿,桂心捧着托盘进来,菜式不多,一笼薄皮包子,一碟凉拌鸡丝,一碟虾籽冬笋,一碗茯苓山药粥,一碗龙须面,另有一盏不知道什么花做的花露,阵阵清香扑鼻。
样数很多,每样都是一小份。
“多谢。”徐幼宁看得目不暇接,说话的声音十分轻快。
桂心见状,只是笑笑,便退了下去。
徐幼宁知道慧心是在笑话她没见识,但她的的确确没吃过这么丰盛精致的早膳,不怪旁人觉得她没见识。
正开心地吃着,桂心推开门进来:“姑娘,奴婢伺候你洗漱吧。”
可她还没吃完。
桂心不是商量的语气说的,徐幼宁只好放下碗筷,由着她领自己去洗漱。桂心手巧,麻利地给徐幼宁梳了发髻,精心描了妆面,领着她出了屋子。
外间像是一间正屋,徐幼宁走出来,便见王福元站在那里。
今日的王福元完全是内侍打扮,头戴三山帽,身着团领袍。
见徐幼宁出来,上前笑道:“二姑娘安好?”
购买专栏解锁剩余51%